 WIKI主页
作者
我的
WIKI主页
作者
我的
 梓歆
平浪风云
地球II
地球Ⅳ
苍星
梓歆
平浪风云
地球II
地球Ⅳ
苍星
| 桂兰共和国 |
| 极东亚国家联盟 | 桂兰共和国的汽车品牌 | 梓歆 |
汉语是桂兰官方语言及国语之一,是桂兰列岛桂兰族及八方族人最重要的语言。本条目主要介绍桂兰的汉语种类及发展历史。
桂兰汉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,东桂兰官话与西桂兰官话。
按照上述分界线以西,再加上州三岛和星洲岛,为西桂兰官话。若是把西桂兰官话在进一步细分,则又分为北角片、九龙片、河阴河阳片、州三片、景云片、西星洲片、东星洲片、南星洲片、橙子片等。
西桂兰官话和东桂兰官话整体上都是以以北京音为基准,以中国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。但是西桂兰官话的发音方面又和东桂兰有很大不同。不同于东桂兰官话的“台湾腔”,西桂兰官话的读音腔调类似“京片子”——读音腔调类似北京,特点就是儿化音非常多。
桂兰汉语中,“街”统一读成“gai”,“鞋”统一读成“hai”。其余与普通话读音大致相同。此外,借鉴外来词的情况比起汉语普通话更常见。
在桂兰语法学界,如果无特别说明,“桂兰汉语”这个词汇,一般是指以小原城上环地区(如今果海市中心一带)的中流阶层方言为基础的桂兰汉语现代标准语,也就是桂兰汉语中的所谓“普通话”。概略说来,桂兰的普通话,就是东桂兰方言-东京畿片的一种变种。因为小原城(今果海特别市)处在东桂兰地区。但保留了一点南方口音(毕竟东桂兰官话的发展,见下),例如“街”统一读成“gai”,“鞋”统一读成“hai”。
以前桂兰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,很多地方甚至两个村都不一定能沟通。各地读书和当官就要学习“官话”去“共通”。“官话”以“官中之官”——也就是首都为依据。桂兰历史上所有统一王朝的首都基本都在平安京,因此“平安京话”就成了“官话方言”——当时的官员通用语。由于桂兰当时学习唐朝,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,平安京人所讲的话是传承自中国“汉语中原官话区”的“古长安音”(古代西安话)。因此,“古长安音”就成了当时的“平安京话”。但在桂兰三国时代以后,统治桂兰的大一统王朝基本沿袭的汉语北京口音,因此“北京音”渐渐取代“长安音”成为桂兰汉语官话通用语。
随后由于政治及战乱等多方面原因,官话“平安京话”开始逐渐蔓延。因而就导致例如果海市和金石滩市——它们上古分别是东桂兰地区的“闽南语区”和“粤语区”。但随着宋王朝的钟离氏大将军在小原(上古果海市)建立“钟离幕府(小原幕府)”——周王朝的前身,很多平安京移民迁居小原生活,因此导致果海、金石滩等东桂兰地区的城市已经变成了“北京语音、但保留闽南语和粤语的发音音调特征”——即演变出了如今台湾腔的“东桂兰官话”。而原本的“平安京话”也变成了“西桂兰官话”。
近代后期,钟离幕府统治桂兰后,东桂兰官话的地位上升,最后以小原城上环的中产以上阶层的“上环话”为基础,形成了新的标准语,也就是越前时代之后的桂兰汉语“普通话”。
桂兰越前维新时期开始西化,开始渐渐出现用汉语词音译外语的词汇。但是当时,汉字词仍然在学者心目中是最高贵的存在。到后来,随着桂兰“全面大力推行西方化”,老一辈受过传统儒学教育的桂兰人不赞同全面西方化,却被认为是“封建余孽、现代化和文明化的阻碍”而全部被杀,史称“桂兰排儒、坑儒事件”。因而全部断代。此时出现的新词就完全用汉语词汇去音译英语,甚至一些本来汉语里有的词也被西方化了。例如“斯达特(开始-start的音译)”,“斯多普(停止-stop的音译)”,“骚达子(士兵-soldiers的音译)”,“索普(香皂-soap的音译)”,“的士(出租汽车-taxi的音译)”,“巴士(公共汽车-bus的音译)”,“德律风(电话机-telephone的音译)”,“火腿儿(宾馆-hotel的音译,但结合了本地文化背景。因为当时桂兰的很多客栈[即古代的宾馆]都提供火腿肉,且hotel与“火腿儿”谐音)”“米尔克(牛奶-milk的音译)”,“嘎斯气儿(煤气-gas的音译)”,“马葫芦(窖井盖/人孔-manhole的音译)”,“卡姆拉(照相机-camera的音译)”及“拖铃巴士(无轨电车-trolleybus的音译)”。
随后很多人渐渐发现,“全面大力推行西方化”实际上带给桂兰的是很多危害,根本不是那些以京畿钟氏钟离铜为首的西化派口中鼓吹的“文明开化”,而是发展成了文化侵略。因此,当时桂兰著名思想家、作家孙盛冈(号平山先生,后来成为桂兰共和国第三任国家大统领)曾经就多次批评这种行为。
举个例子,以‘公共汽车’和‘巴士’为例,本土固有词‘公共汽车’让人一看就知道是‘可供公众乘坐的汽车’,但音译‘bus’的‘巴士’这个词,意义不明。这难道就是那些鼓吹西化的人所主张的‘现代化’和‘文明化’吗?这好吗?这不好,这已经变成了文化入侵了。
古埃及文明,短短几百年内就被基督教彻底覆灭。因为相比前两次的入侵,基督教的方式是拆掉他们的神庙拿去盖教堂,毁掉他们的神像,在上面刻上十字架。毁掉他们的祭文,杀掉他们的祭司,让古埃及文明的传承出现了断层。至此,一个辉煌的国度,就会被彻底的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,就像从未来过。文化侵略就像是寄生虫,在完全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影响着宿主,让宿主得病,让宿主虚弱,让宿主臣服。
当然我不赞成完全的自我封闭,钟离幕府闭关锁国的最终结局就是:桂兰被日本把大门轰了个粉碎。但相比之下某些人宣传的所谓“文化包容、文明开化”是什么形式呢?是以所谓‘高贵’的西方音译词代替所谓‘腐朽’的本土词汇?这对强大我们自身的文化有什么好处,我没有看到,相反的,我知道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之后,以后的桂兰人或许对自己文化的常识会被极大程度的冲刷,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去汉化、西方化。以后他们可能会觉得“说‘hello’就是文明现代的表现,说‘你好’就是野蛮封建的表现。”
对于文化包容来说,桂兰文化必然是包容的,但不是连垃圾都要照单全收,我们向来认同文化交流。我们的桂兰汉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集百家之长。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学习先进技术,进行文化交流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无底线的包容,利于我们,那就吸收消化。不利于我们,抱歉,哪来的,回哪里去吧。
今天某些人在那觉得“以西方音译替代本土词”就是文明开化的体现,还在使用本土词就是封建余孽的体现,我认为,文化包容,不是连垃圾都要照单全收,这叫民族的骄傲与自信!”
——孙盛冈《平山杂文集——论“全盘西化”与“文化自信”》
随后,桂兰开始转变,很多固有的词汇依然保留,不再音译。只有“巴士”,“的士”等词汇因为使用力度大,面积广仍然得以留存至今。例如果海市营巴士、金石滩巴士集团与绘希市营巴士。当然,也有很多巴士公司自始至终一直没有“被文化入侵”,一直保留传统名称,例如“临安公交(临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)”、“京金公交”(京金铁路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)与“柯山公交”[柯山市公共交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]。当然也有一部分巴士公司为了追求一种“文化上的返璞归真”,因而启用了以往的“公共汽车”和“公交”之名。例如桂兰河海省最大的私有制巴士公司“河海巴士”就在2005年4月1日把公司名改为了“河海公交”,“河海巴士”只保留作为通称,该公司的正式名称仍是“河海公交”。(相比之下羽泽民国很多原本称之为“公车”和“公交车”的公司如今却要改称“巴士”,例如2023年1月1日更名“松京都巴士”的“松京都公车”)
孙盛冈也因为理智的思想,加上独特的领导才能,成为桂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,任期从1937年一直到1943年为止。
在1941年桂兰内战结束,由桂兰共和国(东桂兰)统一全国后,孙盛冈随即开始大力推普,制定了新的“桂兰汉语标准音”——以“东桂兰官话-东京畿片-上环小片”作为标准桂兰汉语。至此,基本奠定了桂兰汉语发展至今的格局。
桂兰汉语起初也以繁体字书写,但略有一些不同(例如桂兰繁体汉字中“线”写作“線”),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,桂兰推崇“简化汉字”,桂兰汉语开始使用与中国大陆一样的简体汉字书写。在历史上桂兰还曾出现过“拉丁化汉语”和“汉语罗马字”——以拉丁字母书写桂兰汉语,但没有得到普及。
此外,除了拼音,注音在桂兰也很常用,但不会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中,只是作为辅助手段,桂兰使用更多的还是拼音。桂兰汉语拼音方案与中国完全相同。
| 桂兰共和国 |
| 极东亚国家联盟 | 桂兰共和国的汽车品牌 | 梓歆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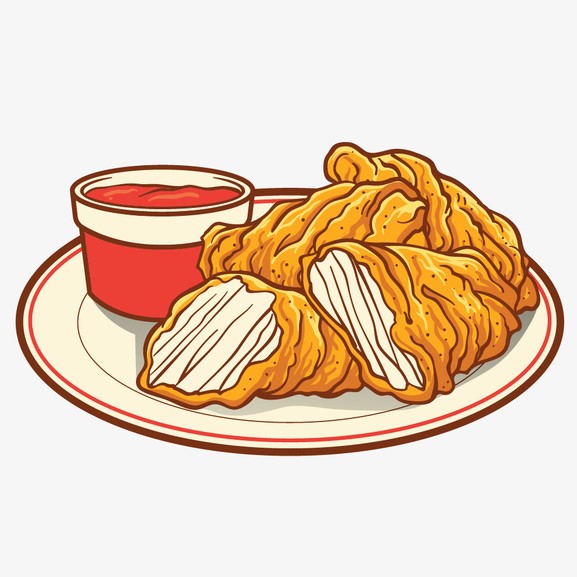 旋头
旋头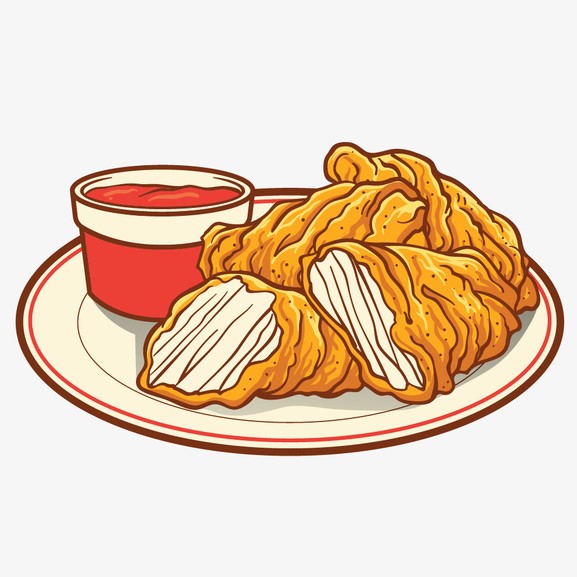 旋头
旋头